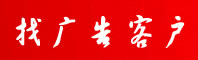利瓦伊伦是法国人Levy-Lambert的中文名字。这个当了13年银行家才作广告的金牛座总裁,是广告公司高层中难得有趣的采访对象。相片由利瓦伊伦提供。
您在作广告之前当了13年的银行家。我们从银行开始谈吗?
银行跟广告业最大的不同在于:银行说,人是最大的资产,但这不是真的。对银行来说,钱才是最大的资产。在广告业中我们没有钱,只有人。我想我从银行业换到广告业,觉得最刺激的就是这一点。
你当初是怎么从银行家变成广告人的?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一天早上我醒来之后,就是不想再当银行家了,而想当广告人。我有了这个梦,就开始跟朋友们说,跟人力中介公司谈。他们都说,维
 Maurice Levy,Pubilcis集团的董事长见了面。我第一次跟Maurice见面,就谈了五个多小时。开完会出来以后,我哭了,因为竟然真的有人会对我的梦感兴趣。五天之后,他给了我一封聘任函,聘我为区域总监,为Pubilcis开创亚洲系统。那是大约六年前的事了。
Maurice Levy,Pubilcis集团的董事长见了面。我第一次跟Maurice见面,就谈了五个多小时。开完会出来以后,我哭了,因为竟然真的有人会对我的梦感兴趣。五天之后,他给了我一封聘任函,聘我为区域总监,为Pubilcis开创亚洲系统。那是大约六年前的事了。所以那大约是1997?
我在1997年6月1日加入Pubilcis。
而Publicis在1998年在亚洲各处展开并购,开始创建亚洲系统?
那些并购都是我去谈判的。因此,今天的Publicis可以说就像我的宝宝一样。而现在他不只是宝宝了。已经在蹒跚学步,跑来跑去,什么都碰一碰,把自己不该放进嘴里的东西放进嘴里。探索世界,很快地学习、成长。而我们的竞争者,有的正在他们的40岁,开始发胖。有的正在50岁,已经发作过心脏病。有的甚至已经70岁,到了人生尽头。而我们却像6岁的孩子,正蓬勃生长。真是太迷人了。我们越成长,越了解竞争者,我越发现我们在Publicis所有的精力和内在的火焰,一定能让我们非常成功。
在经营Publicis亚太系统上,目前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目前最大的任务是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在合并之前的Pubilcis在专业上应该可以更加强。而D'Arcy则应该可以有比较多长期合作的客户。我还在建构适当的组织。但已经差不多要完成了。
比较明确说明的话倒底是哪方面的工作呢?
找到适当的人。找对经理人,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找错人的话,什么问题都会发生。
你用人的考虑有哪些?
我信任自己的直觉。通常我一分钟内就可以下决定。首先最重要的是信任。我没法忍受对我说谎的人。我曾经因为有人说谎而开除他。因为如果你说了一个谎,你必须说更多的谎来圆谎。这样不可能产生什么可以当作基础的持续性的东西。这是基本的道德价值。我并不想找从前做过同样工作的人。事实上,我更想找从前没有做过同样工作的人。如果有人告诉我,别担心,这种事情我以前做过,我不喜欢听到这种话。因为我们这一行就是要有创意,即使是在我们经营事业的方式上。创意就是要做不一样的事。事实上,Maurice Levy雇用我的这件事,就展示了这一点。当Pubicis要发展他的亚洲系统时,他可以雇用很多从麦肯,奥美,等等在自己的公司内排名二号、三号,而想到Publicis来排名一号的人。可是他选择雇用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做过。他也知道,如果是我来做的话,更能够做出真正的Publicis的方式。因为我们很迟才进入这个市场,如果我们想要成为另外一个麦肯,首先,我们做不好,其次,市场也不需要另一个麦肯。这个市场事实上不需要另外一个广告代理商系统,这个市场需要的是另一个系统。我认为Publicis提供了这种「不同」。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作业方式。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承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成长的比别人快。
你们成长的比别人快应该主要是因为你们从事的并购吧!
是没错。可是我们能够进行并购也是因为我们成长的比较快。因为并购需要钱,我们的钱就是从我们的经营而来的。我们的系统比别的系统成功。
可是之前的Publicis可以说是相当的沉寂?
没错。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比较谦虚。我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客户出名,不是让自己出名。我觉得我们的竞争者相当自恋。他们喜欢到镜子前面去说,「镜子,镜子,我是不是世界上最有创意的?」他们去参加那种其实只是广告人相互评审的广告奖。我倒觉得由客户来评审广告公司比较有趣。事实是,我有点忌妒,我没有得很多的广告奖,我没有很多的声音。因为当然我也很想听到人家说,维伦,你们公司是亚洲最棒的。可是,更重要的还是得到客户的认同。得到新业务。
在你们与D'Arcy合并之前Publicis的自体成长(organic growth)的比率是多少?
我想我们每年的自体成长都高于市场成长。例如,2001年度我们的自体成长比率是3-4%,2002年度我们的自体成长约1%。而这两年市场是萎缩的。成长则来自于国际客户持续给予更多的业务。如我们得到雀巢在泰国的Coffeemate业务。我们获得了HP原来的Compaq业务。Compaq本来有自己的代理商FCB,所以他们把业务给我们说明他们认为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可能比较沉寂,但是那是因为我选择先用作的而不是用说的进行我的工作。理想状态当然两者都可以并重,我也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注重形象的产业。不过我喜欢这个想法:大家先不注意到我们,以为我们是家小公司,忽然之间才发现到我们原来是巨人。我们的商标是狮子,我也认为我们将是竞争者的起床号。
Publicis要怎么建构自己的声誉?以Publicis旗下的代理商来说,李奥贝纳有李奥‧贝纳,上奇,不管是好或不好,有著名的上奇两兄弟的传奇。而我们对法商的文化和法国的广告历史一般欠缺认识。比如Publicis的创办人据说是法国现代广告之父,我们对他的事迹却一无所知。英美文化的宰制性对你建构Publicis品牌的任务有什么影响?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重点不在于法国文化跟美国文化的对抗,而在于对于世界的观看方式。一种是同质化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观看方式:大家都说英文,大家都吃大麦克汉堡。一种则是我们说的“La difference”,大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组合,大家都能相互沟通,但不必经由母语。英文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你的母语,可是我们能够相互了解。不只是因为经过书写的语言,还有口语,目光的接触等等──沟通是件很复杂的事,不只是用语言的。正因为我们来自一个不同的国家,正因为我们在法国有很强的如烹调、服装等等的根源。我们知道不是每个人对世界的观看方式都相同,因此我们对于别的国家有更真挚的尊重。我们知道台湾跟法国不一样。台湾跟中国不一样。台湾就是台湾。可是,我们也想找到一种台湾人之间相互沟通中的普遍性,让我们能替客户接触到台湾消费者的心,做好我们的工作。
您想把Publicis建立成一个法国的广告公司吗?
我们的口号是说我们「来自法国,欧洲天性,走遍天下」(French by birth,Euporean by nature , global by calling and by reach)我们希望Publicis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不过这不是有点矛盾,甚至有点套套逻辑。你得有些什么东西作根据不是吗?如果你不让大家看到你们的法国性,大家怎么知道你们是谁?毕竟你们说的是La difference. 不是La différence或The difference。
我们希望大家知道我们是法国的,Maurice毕竟也选了一个法国人来经营亚太区。我记得Maurice Levy到我的母校演讲时,曾经说道,如果一切条件均等,他希望自己的继任者是法国人。因此我们并不讳言我们来自法国,我们对这个事实非常骄傲。我们的总部就在巴黎的凯旋门旁,这对我们也非常重要。而La difference的La也是法文。我们的兴趣在于找出什么是法国性中的普遍性。法国可能是傲慢的,自我的。我们有兴趣的是发扬光大法国性中的另一面:法国给了世界人权的普世价值,法国人想要让世界比较平衡的野心,还有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要努力工作,也要好好享受。享受美食,艺术之美,重要的不是只有钱,还有生活,法国文化中的浪漫之处,等等。
我读过的数据中说Maurice Levy采取的管理方式是自由放任,只要最后有达到所要求的数字目标。是真的吗?
不完全是。我想我们对于数字不是目标,而是结果这一点都有很清楚的认识。数字是工作质量的衡量,就像小时候上学会有成绩一样,成绩不是你学到的东西,而是对你学到的东西的认可,对学习质量的衡量。因此由市场和客户方面得到数字性的认可,我们通常能如约获得客户的适当报酬。那是因为我们对于替他们增加生意真正有所贡献。因此能达到数字要求的广告代理商,就是达成诺言,产生消费者注意得到的差异的代理商。
你曾经做过13年的投资银行家,如果从投资银行家的观点来看,会投资在广告业吗?
我加入Publicis不久,有个机会可以投资Publicis的股票。我就把我所有的储蓄都买了Pubilcis的股票。我没有思考,只是就这样作了。
那是你个人出于爱和热情的选择,我想知道以一位前投资银行家理性、分析性的观点,是否会投资在广告业上?
是的。我还是会投资在广告业。现在的市场对于传播与广告业类股票的价值严重低估。首先是整体的全球股票市场都不景气。其次,又有那些作帐丑闻,如我们竞争者之一的Interpublic集团必须重新提列帐目,给我们这个类目的市场增加了不必要的疑虑。因为还有很多的传播集团如Publicis在各方面都经营得很不错。不过话说回来,我已经不是投资银行家了。而且当初我不想作投资银行家的理由之一就是因为教别人投资不是件好事:别人如果因为你而赚钱,觉得是理所当然,因为你而赔钱,就是你的错。所以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理财的:我1/4的财富都在Publicis的股票里长期持有。我不是很有钱,所以我的个人持股大概只有Publicis所有权中的百分之零点零一。是个小小投资人。但是我是位很骄傲的投资人。因为我在那里工作,我跟这个品牌有很热情的关系。而且我知道,也许有一天我会换工作,但我绝不会换到其它任何广告公司去。就像我在银行时我为同一家银行工作了13年。我无法想象我怎么能前一天跟客户说我们巴黎银行是最好的银行,第二天却说我到别的银行工作了。我把我的全心都给了Publicis和我们的客户。
你为什么说也许有一天你会换工作?
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6年前我换工作的时候,整个过程太有趣了,我告诉自己,这辈子有机会应该至少要再这样作一次!当时我还不相信灵魂转世的理论,可是那种经验就跟转世一样,不过是在同一个人生中。人生最棒的事情不就是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应该再这样作一次。
你也可以考虑搬家,比如说搬到中国去。
喔!不,我不认为我有勇气这样作。但是我认为我的继任者应该以上海为根据地。我认为上海真的是个具有超级活力,任何具有野心在这区域有所成就的人都不可错过的城市。我不会搬到上海,因为我不会说中文,我的生活重心都在新加坡。或许这是某个别人的任务。虽然Publicis亚太系统是我的宝宝。它现在已经是个幼儿了。等到他到了青春期,也许就需要一个新的家长。虽然我对于亚太区的判断是,5年之内,或更快,亚太区经营的重点就会转移到上海。不过这跟我们中国办公室的成功程度有关。不过我们重新建构新加坡办公室的经验,已经将原来一家本地公司成功转变为一个能够担负亚太区基地的办公室。新加坡作为Publicis亚太中心的日子还很长。甚至如果当我担负起Publicis全球系统中的任务时,我也希望能由新加坡操作。
新加坡有什么地方是别的地方,如台湾,及不上的,而不能享有同样的发展愿景?
首先,新加坡具有政治稳定度。这点台湾没有。这不是台湾的错,而是历史的结果。台湾没有新加坡所有方便的交通。比如台湾到上海至今没有直接航线。而我希望这一点早点解决,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新加坡也有很好的传播建设,和很好的航空公司和机场,优越的基础建设,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并有各种文化与民族背景为新加坡带来很棒的多元性的优点。新加坡还有能干的政府,文书、税务都非常简单,税率也低。这些都让新加坡具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这些不代表台湾就没有成为传播或广告中心的可能。今天早上我给台湾的Publicis员工一个任务:我希望台湾Pubilcis成为第一个创造出在全球播放的广告影片的办公室。创造出具有本土消费者洞察,却也有普世吸引力创意的例子,现在是在电影,而不是在广告影片中清楚地显示出来。我非常欣赏的李安导演,就是个出自台湾,而征服世界的例子。
你给上海和香港的Publicis员工的任务是什么?
香港现在的情势相当艰难。我很喜欢香港,我在香港住过4年。现在的香港显然失去了某些东西……或许是一种自信。或许香港本来是个过度自信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能重新获得过去的那种活力,应该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我给香港Publicis的经理人的任务之一,是保持本地与香港大亨集团之间的业务的平衡。如我们现在从香港经营UPS等、西联银行Western Union等的业务。至于中国,他们的任务非常不同。中国有点像欧洲,事实上就像有非常多的国家。他们有共同的书写语言,却有很多种方言,和很大的郊区。大家都只开始碰触到「中国挑战」的冰山一角而已。我们在中国的最大困难是因为当地的传播业刚才起步,我们还没有办法像在其它市场一样找到足够的人才。这个市场还会持续提供台湾广告人发展的机会。但我希望更多的台湾广告人愿意留在台湾,因为台湾市场也还在继续成长。总之,我们在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次一世代的本地人才,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管理人。因为迟早中国(客户)和别的地方一样,都会希望由本地人才经营他们的业务。长期来说,我们一定不能靠外籍人才。同时我们对经营中国市场也要抱着实际的态度。要有一个将来能经营全中国市场的模式,而不是只在上海发展。Publicis集团在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盛世长城在中国排名第一,李奥贝纳排名前五。我们的媒体公司很强。跟我们有换股合作关系的电通也排名前五。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建立Publicis的品牌。
回头谈谈您的生涯选择,为什么当初会想做广告?你对广告的印象本来是什么?
首先,我发现我对在银行作的事情已经不感兴趣了。我发现自己对纽约昨天晚上的收盘指数一点都没有兴趣。我问自己,如果我能找到一个我对它的产品有兴趣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认为,让消费者决定购买雀巢咖啡而不是其它咖啡的因素,比起让IBM计算机股价上涨或下跌的因素,要复杂得多了。
所以你是从以钞票为产品换到了以雀巢咖啡为产品。
这正是六年前我对自己生涯转换的叙述:从钞票到雀巢咖啡。
那你对广告的看法在加入广告业之后有些什么改变?
有一点。首先,我本来并不了解这行业有多难。我的梦想本来都是关于广告魔术的那个面相。我以为我本来当银行家已经是工作非常努力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进到广告业我必须还要更努力。我对广告本来有个很浪漫的想象,以为我的工作就是跟朋友一起围桌而坐,动脑想点子。现在我知道直觉很好,可以深入探讨,除此之外却也还需要纪律,调查,努力工作。有一次我跟Murice Levy抱怨,说「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工作有这么难。」他的回答是:「要是我告诉你,你就不会接受这工作了。」我想他高兴雇用一个从没做过广告的人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样这个人才会低估面对的困难。事实上他有一次也跟我说,「你能把这工作做好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